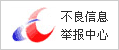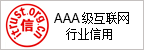新京报报道,近日,唐山廖海军案的办案民警、刑警队长张宝祥因涉嫌刑讯逼供,被唐山市路北区监察委移送审查起诉。有媒体称,这是目前公开披露的首起对冤案中的刑讯逼供启动刑事追责的案件。
廖海军案算是陈年旧案:1999年1月17日,唐山迁西县两名女童被害身亡,17岁的廖海军被认定为杀人嫌犯。2003年,廖海军及其父母被唐山中院以故意杀人罪、包庇罪,分别判处无期徒刑、有期徒刑五年。2018年8月9日,法院改判三人无罪。
值得注意的是,廖海军此番以“被害人家属”的身份收到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追究的是民警张宝祥对其父亲廖友刑讯逼供的法律责任。另据媒体报道,张宝祥还是廖友的同学。
近年来,诸多陈年旧案得以平反昭雪,也不乏昔日办案人员因各种原因落马被查,但像廖海军案这般指向如此明确的冤案追责步骤的还不多见,对刑讯逼供者启动刑事追责,更是具有标志性意义。
事实上,早在2016年,中央政法委就强调,对因刑讯逼供造成冤假错案的,必须追究司法责任。公安部同年修订的《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也提出,如果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存在因刑讯逼供、伪造证据等故意造成执法过错等情形,相关责任人将被从重追究执法过错责任。
但在实务中,追责刑讯逼供非常罕见,主要原因是追责机制滞后。廖海军案刑讯逼供发生在近20年前,但直到改判无罪才启动追责。时过境迁,证据遗失、事实难以还原,还有可能受追诉时效的影响。另外,对刑讯逼供类案件,目前首先启动调查的是公安督察体系,也可能会受到干扰和约束。
更重要的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中,一些办案人员存在根深蒂固的有罪推定观念,认为适当刑讯逼供是办案的必要措施,因“职务行为”被追究刑责,阻力之大不难想象。
但随着“重证据、不轻信口供”规则和“疑罪从无”原则逐渐确立,严禁刑讯逼供、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要求也日益严格。今年2月,最高检制定下发《2018-2022年检察改革工作规划》,提出“建立重大案件侦查终结前对讯问合法性进行核查制度”,同样是着眼于审讯过程的合法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廖海军案办案民警张宝祥被追究刑责,是个重要的节点。
廖海军案有其特殊性,其父母都已去世,而从法院告知书看,此次追究的是对其父亲廖友的刑讯逼供。这主要是由于廖友伤情、医院病历、唐山市人民检察院的核查结论的存在,这也为启动追责提供了“硬核证据”。
但这不乏普适性启示:冤假错案追究刑责,还是要依赖于证据,而不仅是被害人的申诉。这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在于,要注重双方面的证据,一是办案民警要重视“自证证据”,确保审讯过程全程录音录像,提外审也应使用执法记录仪;二是,犯罪嫌疑人注重证据的固定、保全和收集。
这在以前或许有不少困难,但随着2018年刑诉法的修订,首次明确了犯罪嫌疑人的“被告知权”和“律师在场权”。这意味着,刑讯逼供将不再是一个神不知鬼不觉的“幽灵”。
严厉追责刑讯逼供,是对冤假错案最有效的“复盘”。酿成冤案,多是一个链条上的错误叠加,只有真正逐项倒查、逐项追责,才能实现完整意义上的正义。通过严格追责,也可以找到漏洞、明确边界,从而完善刑事诉讼程序,增进司法公正。
由此看,“廖海军案”不失为一个突破口,未来“追责难”的问题或将随着类似案例的出现、法治环境的完善,进一步得到解决,进而建立起常态化的追责制度。对司法人员而言,这也是一次重要的提醒——防范刑讯逼供并不是约束和限制司法人员,更不是打击办案的积极性,而是强调依法办案,从根本上保护司法人员免受追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