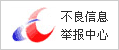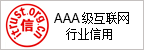赵东方给故友孙坤鹏打了一个电话。他得知这位多年未见的朋友已经在义乌从事服装生意,3岁的孩子在老家开封上了幼儿园。
3年前,赵东方决定拍摄一部郑州城中村拆迁纪录片的时候,孙坤鹏被选定为故事的主角。他的纪录片里出现了庙李、刘庄、邵庄、高皇寨等村庄,有拥挤脏乱的街道、逼仄的出租房、幽暗的楼梯道、不时闪灭的顶灯。
【前奏】
城市的发展终将扫除某些原有生态,那些循环播放拆迁政策的宣传车,已经拆除的残墙,早已换了景象,取代它们的是拔地而起的高楼。
2019年9月2日,郑州市金水区兴达路办事处黄庄村,今年7月份拆迁
孙坤鹏和他的朋友也已离开郑州,当他们向房东交还钥匙的时候,可能想不到被拆迁的人们也将开始流动,甚至也将面临财富迅速增加后的迷惘,也将为扑面而来的新生活重新计算和纠结。
郑州市的城中村改造从2003年启动。在2010年~2015年,郑州市共启动拆迁村庄627个,动迁175.65万人,全域范围内保持着每年拆迁100多个村的进度。
赵东方拍摄纪录片这一年,张家村作为最后一个都市村庄改造项目动工拆迁。这意味着,从2016年开始,郑州四环内再无城中村。
城市的扩张还在继续,郑州已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GDP和人口总量上创下新纪录。
2019年8月份,郑州公布的最新拆迁地图再次引发一阵骚动。当人们最早说起“拆迁户”时,总会联想到出暴发和膨胀,甚至“拆迁户”赌博、吸毒败家的新闻偶尔会见诸报端。事实上,这种“幸存者偏差”导致的成见正在逐渐消失,就像郑州已经走过最轰轰烈烈的改造阶段,被拆迁的人们心境和生活也趋于平静。
告别都市田园
“请主动自行搬离,以免对您的经营和财产造成损失。在此期间,对于非法生产经营、欺行霸市,危害群众生命财产的商户,我们将依法坚决予以严肃处理或打击。”在赵东方拍摄的《真实记录郑州城中村拆迁》纪录片中,一辆白色宣传车循环播放着拆迁宣传,旁边是来往的电动车和匆匆而过的行人。
2019年9月2日,郑州江山路三全路,老鸦陈村老年过渡房已搬空
2015年夏天,郑州老鸦陈。杜文涛是高考之后一周才注意到这种宣传车,以及街头巷尾议论拆迁的邻居。这时候,家里已经要搬走了。 杜文涛家里的4层楼,每年能带来超过10万元的租金收入。拆迁后,按家庭4人赔付480平方米安置房,80余万拆迁款。
作为城市流动人口聚集地,和老鸦陈一样,郑州北环的多个城中村都有不菲的定期租金收入。其中包括“中原小香港”陈寨、刘庄、马李庄等等,很多村民的楼房能盖到将近20层,迎接着一批又一批的务工人员、刚毕业的大学生、做生意的小贩。
老鸦陈本地人口约1.5万,流动人口最多时有逾20万。
2019年9月2日,郑州江山路三全路,老鸦陈村拆迁后,昔日的村庄如今是一片平地
杜文涛在这里渡过了18岁前的美好时光,他的玩伴主要来自家中的租客。放学回家,五六个玩伴在暮色中疯跑、捉迷藏,路边的小楼成为最理想的藏身处。
父亲喜欢喝酒,经常叫租户来喝酒聊天。家里做包子、油条等,母亲就会让杜文涛送给租户一点。
这种像暮色一样逐渐远离的记忆,掺杂有最普通的生活细节,比如家里经常去租户的商铺买鸡蛋、猪肉;比如一对经常吵架的小情侣,因为没钱支付房租,在杜文涛家人外出时卷起行李离开。
杜文涛上幼儿园之前,门口还是土路,2002年前后成为水泥路,再往周边房子增高为多层小楼,对外出租。小吃摊越来越多,外来人口逐渐聚集。穿过老鸦陈的江山路热闹起来,路上的车辆越来越多,公交的线路越来越多……
“我们是不舍的。”那个夏天的夜晚,杜文涛一家人散步时看到家里被拆除的门窗,生出回家居住的念头。但也只是一个念头,因为新生活就要开始了,尽管一切来的猝不及防。
31岁的郑东新区祭城人李华强的回迁房已经入住7年,他对老家贾岗村的记忆是田地、鱼塘和两层的自住房。不同于城中村,10多年前拆迁时当地没有什么高层,村民以种地为主。
由于拆迁早,位置接近城市边缘,一部分村民最早对相对较低的拆迁补偿并不满意。但如今村民都搬进了新小区。“最直观的是环境比以前提高,生活更加便利了。”无论如何,村民们较早享受了城市化带来的红利。
一定程度上来说,回迁在地理上改变了原有的村庄式人际生态。
原本一家人同住院落的相处方式,变成了同一走廊里两代人门对门的“邻居关系”;村子里的堂亲由此前散状分布的鸡犬相闻,转为以楼号、电梯为符号的现代社区形式。
这种改变带来的影响是双面的。搬入回迁房后,李华强和亲戚们更近了,属于从这栋楼到那栋楼的距离,在小区经常见面,也经常走动;也有因此产生矛盾的家庭,兄弟俩分房子闹矛盾,争论父母的房子应该给谁;也有分到房子后沉溺于赌博的,最终沦落到变卖房产。
杜文涛离开老鸦陈时,没有来得及和朋友们一一告别,在江山路上打闹的玩伴大都像梦一样跑丢了。唯一能联系上的玩伴现在是他最好的朋友,家里在郑州买了房,就职于一家广告公司。
他们像以前一样,经常一起玩游戏,寻找新开的餐馆,驱车去开封游玩。
城市流动人口
杜文涛所谓的搬家,是在自家的耕地边搭建活动板房。尽管每年手握数万元的过渡费,但很多老鸦陈的村民们都首先选择搭建临时房屋。杜文涛的家人在板房里住了一年后,租进了社区楼房。
按照目前的施工进度,家里的回迁房2021年前后才能入住。杜文涛已经搬了三次家,现在他们居住的是年租金2.3万的三室两厅。他的朋友中,因为开发商烂尾等原因,已经在外“漂泊”了10年。
和很多人想象的不同,拆迁后,沙门村人陈国庆的收入有所减少。陈国庆家有一栋13层高的小楼,对外出租房屋达100多套,每月租金收入约8万元。拆迁补偿面积1200多平,除了自住,交房后的对外出租月收入3万左右。
按照陈国庆的算法,沙门村属于楼层高,外来人口多的城中村,村里每家楼高平均10层,每层约10套,整体上平均每家月入租金6万元左右。而现在郑州租房市场低迷,一室一厅现才租1000元,自住外的回迁房产租金每月才2万多元。
陈国庆也了解到,家中拆迁的年轻人贷款买房、买豪车,但原来的固定房租收入减少后,缺失了最重要的资金来源,不再敢出去乱吃乱喝。
2008年前后,大量人口流入郑州。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10年约有流入人口160万人。沙门村这些10多层的出租房大都兴建于此时,而之前村里的房子以两层为主,盖一栋楼需要100多万元,很多人对外借钱盖房,期望借助城市发展带来的机遇增加收入。“后来2016年一部分人成本可能还没收回来,就拆迁了”。
在房产交付之前,政府部门会发放一笔过渡费用。拆迁家庭从此开始了郑州市内的“流动”,今年7月份交付新房的兴隆铺村民中,很多人为尽早结束这种“漂泊”,拿到钥匙后直接搬入毛坯房,同时进行装修作业。
45岁的陈国庆细数了身边的拆迁朋友,总结出两种迁徙轨迹。“有三分之一的人本身家庭条件不错,盖房子借的100多万已经还完,拆迁前几年就买了商品房,拆迁后直接搬去居住;另外三分之二拆迁时没有购买商品房,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家这么多房子,没有必要再买房。所以拆迁后只能在外租房住,也就造成了很多人回迁房交房后直接搬入毛坯房”。
陈国庆见过很多处于拆迁与回迁过渡期村民的生活状态:
“我家亲戚一年能搬家好几次,比如签租房合同半年,到期后房东要求涨价,亲戚不能接受,就得再次搬家。村民在外租房很不稳定,除非一次交3年房租才不面临涨价带来的风险。”
“今年5月份,我去邙山路过关庄村,看到有些村民在菜地里用保温板搭盖临时房,一家几口住在里面。我停下车询问,他们说家里拆迁了,住地里是为了省钱。”
迷失是少数的
王景镇是在郑州帝湖边上的一辆面包车上接受的采访,1小时的时间内他接打6个电话,回复4次微信。
2014年,后河卢村拆迁时,他27岁,开过婴幼儿游泳馆、宾馆、台球俱乐部,但没有赚到什么钱。“小宾馆多少挣点,台球基本上每个月赔钱,游泳馆前两年挣点钱,后几年赔了。总体上就不挣钱,耗费几年,但就是天天很忙。”
面包车百米外就是后河卢村,村民们的回迁房建设接近尾声。王景镇能清楚地指出附近原有耕地、葡萄园、菜园等的具体位置。2002年左右, 帝湖花园项目逐渐建设,当初的水库被修建成帝湖,后河卢村逐渐名声在外,配套设施的兴起带动了外来人口流入。
房租收入曾经也是王景镇家的一大来源,拆迁后家里预计分到大小6套房子,但他多次提到压力大。“也不是没有吃的没有喝的,人的压力取决于欲望,我现在有家庭,两个孩子,得出去创业。在生活和工作上都有压力。”
王景镇有一份清闲的工作,同时在做建材生意,所以下班时间比上班时间还要忙。他身边的朋友大都是村里拆迁的发小和同学,闲暇时三五个朋友一起打球、打牌。朋友们也在做自己的事业,有自己的工作。
“有在家不工作的,偶尔出去上网。其实不上班的这一部分人也想挣钱,但是没有好的项目。门店雇人、交房租、物业费、水电费等各种费用消耗大,基本赚不到钱,甚至赔钱很常见。这有什么意义呢?就是拿钱换经验。说句心里话,创业的目标是为了挣钱,但是做生意亏损,只能安慰自己说是攒经验。”
他的微信签名是“努力+勤奋=奇迹”。10多年来,在他的内心深处有一个目标:能买一套属于自己的商品房,一辆70万左右的车。
去年王景镇东拼西凑买了一套110平方的房子,每月背负房贷,车仍旧没有更换。他认为定下的目标只能算实现了一小半。
多位拆迁户对快速到来的财富持谨慎态度,他们会认为这是上一辈的心血和资产,不能轻易挥霍。
除了自我约束,王景镇还在意来自外界的评判:其实完全可以通过卖回迁房达到自己的目标,但是没有意义,如果卖掉一套房子,就会眼红200平的房子、200万的车,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才会更踏实。自己的房子,在朋友、亲戚、领导看来,是通过努力换来,而不是通过“变卖家产得来的”,这是两码事。
没有事业的拆迁户大都沉溺于游戏、酒吧和赌博。祭城人李华强告诉河南商报记者,附近一个村很多年轻人上完小学就辍学步入社会,他一个23岁的远房亲戚因为玩游戏、赌博,家里分的4套房子都卖了,现在父母住进了地下室。
“有些人太沉醉于打牌,通过朋友介绍赌博地点,一天输几十万很正常,输了钱就去借高利贷,越陷越深。尤其是小学毕业的孩子很叛逆,家里分了几套房就觉得厉害得不得了。”李华强说,村里有孩子向父母要钱,不给钱就反应激烈,有时候电视剧里的情节并不是假的。他们的心理是觉得家里有钱了,大不了卖一套房子。
身份认知
“我们年轻时偶尔也去唱歌、酒吧,打牌,但是沉溺于此就不好了。”王景镇认为,他只是普通家庭,不是家里做大生意或者背景深厚,没有天生的光环。如果拆迁户是一种身份的话,它并不能带来什么。
河南商报记者直接采访的9位拆迁户及周边人的观察中,诸如挥霍沉溺玩乐、声色犬马的拆迁户并不占多数。“我和身边的朋友,从来没觉得家里拆迁带来心理姿态的变化。我朋友还有分2000多平方的,我们认识新朋友的时候,从来不提拆迁的事情,从来不说自己家多厉害,家里有多少钱,家里拆迁分多少房。”
“对我们来说,不会想着自己家里拆多少房,自己觉得多牛。也没有说别人家不是都市村庄,就有其他想法。当然我们也不在意别人的看法,不怕别人看不起,因为我们就是普通人,没有去看不起谁,也没有多卑微,就是这样。”
2019年9月2日,郑州市金水区兴达路办事处黄庄村,今年7月份拆迁
郑州市公交四公司车长薛峰7月份刚刚签完空房协议,老家所在的黄庄正在被拆除。薛峰选择了继续在公交公司上班,他的想法是,不工作也能继续生活,但“在家无所事事,土地也没了,可以想象就是天天在街上闲逛,就像行尸走肉一样”。
薛峰的工作岗位是位于郑东新区的170路公交线,每天经过以龙子湖为中心的南北向17个站点。他见证了郑东新区从无到有,再到今天的繁华景象。沿线经过一片片高楼时,他会想起这里曾经的草房、瓦房,以及他和发小骑自行车上学的场景。
现在,薛峰和另外8个关系好的发小有一个微信群,他们来自附近的薛岗、陈三桥、磨李、贾岗等已经拆迁过的村庄,职业包括工程、公司司机、餐饮、教育行业等。
意外的是,薛峰提到的拆迁后欲望增大的行为是:租房时丢弃原来的老沙发,新买了一套沙发;想换一辆20多万的轿车。“我们是村里的孩子,从小的思想观念、消费习惯都相对保守,没有太大的消费野心,实际上现实也不允许挥霍”。
郑州市一处公交场站调度室的员工谢菲能接触到每一位来此打卡的司机,她的印象中,每一条公交线上都有数位拆迁户,但是他们和其他员工一样勤恳,并未表现出更多的姿态。 “我觉得大部分人对拆迁户有误解,我们线上一大半是拆迁户,但是他们都在认真地工作,和拆迁之前没有区别。工作可能对他们来说可有可无,却是一种生活的价值实现。或许因为人生追求的不只是金钱,还有一种寄托。”
杜文涛对“拆迁户”这个词保持中立,他认为自己本身是“拆二代”,和对“土豪”这个词一样,一开始人们说出“拆二代”的时候,会有一种不屑或羡慕嫉妒,后来这种称呼演变成一种调侃。一部分人因为拆迁自觉或不自觉地改变了消费观、人生轨迹,金钱对他们的影响太大了。有时候我也会给朋友开玩笑说自己是“拆二代”,但实际上我内心认为那些钱是父母的,而不是自己的。
拆迁户是城镇化催生的一个群体,这个群体诞生在地区发展最快、社会矛盾最尖锐的时期。他们的经历和心路,和一座城市的心跳紧密联系在一起。
郑州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拆迁户了,因为外界的成见正在减少,拆迁户的浮躁正在褪去。尽管郑州四环内的城中村改造已经结束,驱动城市发展的地产和基建建设仍在向外蔓延,但和城市的发展规律一样,拆迁户这一群体正在趋于冷静与平和。
(应当事人要求,文中除赵东方、孙坤鹏外,杜文涛、李华强、陈国庆、王景镇、薛峰、谢菲等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