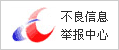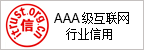对唐河的眷恋,来自对一条支流的依恋。
这条支流,叫桐河。和唐河一样,桐河乡因河而名。
记忆中,故乡桐河乡南蛇湾村每到秋季汛期时,村庄总是被四面的洪水所包围,尤其是东河湾的水似乎是漫到了天际,一眼望不到边。混沌的水流中有被淹死的猪羊在漂浮中急剧而下,还有麦秸垛、树木、杂草、庄稼、西瓜等物夹杂在其中,也有一些长蛇、蟾蜍缠绕爬行在上面,真正成群的鱼倒没有见到。
现在忆来,那场景壮观而凄凉。
洪水消退到那里去了?我不知道。只记得大片的苞谷、芝麻、高粱伏在地里,直不起来腰杆,河湾沟渠内的鱼蟹倒多了起来。我和村里的伙伴们拿着盆桶铲把小水沟分段截堵,舀干里面的水,鱼虾蟹鳝便成了我们捕捉的美味。但偶尔也会遇到长蛇混在其中,倒也不惧,伸手把它甩到一边的庄稼地里,那蛇便哧溜溜地不见了踪影。
村里很多麦场秋场离河流很近,我跟着奶奶和父亲,妈妈经常夜里在场里看护苞谷、芝麻、黄豆、花生,倒没有人偷,怕的是成群的猪羊来糟蹋粮食。
常有弯月悬挂天空,听长辈们讲一些传说故事,记忆深的便是一个叫宋定伯捉鬼的故事,大意是宋定伯走夜路,遇到一个鬼,最后在背鬼过河时套问出来了鬼是最怕河水弄湿脸面的,弄湿了便脱成畜生,投胎不成人了。宋定伯又听这个鬼说投胎后要大开杀戒,报前世之仇。他便把这个鬼按在了河里。拖上岸时,这个鬼变成了一只羊,宋定伯牵着它到集市上卖了。
这个故事使我常常幻想着宋定伯在河中把鬼死死摁住的场景,那是多么可怕而畅快的事呀!于是,对河流又多了一份敬畏与神秘。还有那个河又阴又缠等等,总觉得河流中有很多看不见的东西在涌动,尤其是酷暑难耐的中午和深夜时,那些令人汗毛直立的河流与鬼神的传说总是让我对河流既恐惧又向往。南蛇湾村还有晌午头、鬼露头,后半夜、鬼拍手,河会吃小孩子等俗语传说。桐河乡还有沿河九十九个大潭涡的传说,还有门板似的大鱼,千年的鳖精,鸡杀人鱼放火等民间故事,纵横交叉的几十条河沟、几十座老桥、几十处河湾孕育着这里的群众,增添了众多美丽的传说。
这都与河流有关!这为我后来的文学创作积淀了厚重的素材。无论是小说,散文,或是诗歌,我都是以河流为主的,文字里无不饱含着对河流的深情,对河流的牵挂,对河流的思念和倾诉!因为河流给了我童年时最浪漫的记忆,最美好的欢乐,最长情的牵挂,最走心的依恋和歌唱。
我怀恋那里的村庄,庄稼,树木,老桥,老井,老屋……但最多的还是河流弥漫出来的气息与味道!
虽然,现在这些河流已不是原来的模样,村庄已不是记忆中的模样,包括空气也不是以前的味道,但这些却愈发使我内心深处的那种气息愈加浓厚、愈发醇香。
我始终相信,有河流的地方一定有灵气在孕育。中国的考古大家徐旭生不就是从水乡桐河走出去的吗?哲学家冯友兰不是从山青水秀的祁仪小镇走出去的吗?他的哲学思想千年以后仍然会熠熠生辉;从这个小镇走出的诗人李季,他《王贵与李香香》是一个时代的歌唱;还有现代著名作家马新朝、田中禾、陈涌泉、杨稼生、汗漫、曲令敏等等,他们的村庄、乡镇、县城都有一条河流在日夜流淌,汲取着天地之精华神韵,使这方水土养育的人踩着家乡的泥水,趟出唐河成就大家。
我还始终相信,有河流的地方一定会滋润着人们勤劳、善良、勇敢、拼博、进取的人品,而且这种有着中华美德的品质一定会代代相传。
我还始终相信,在河流身边生活的人们,河流对自己美好生活的影响、回忆、留恋、牵挂会伴随其一生。当他年迈时,他仍能随着记忆回到儿时的河流中,在那里倘佯,在那里玩耍,在那里牧牛,在那里歌唱。
而河流,那永不停息的的奔淌,凝结着对过往的追溯,对现实的见证,对未来的期许。唐河在河的奔涌中,也演绎出了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在奔腾的岁月中历久弥新、历久弥坚。
这是河流的骄傲,也是唐河人的荣光!
河流啊,你永远流淌,也被永远铭记。那水花四溅的梦境,是岁月留下的醉美和声。
这和声,沿着唐河这条河流的入口一一源潭镇小王庄处鸣唱,在沿岸村庄的变迁、民俗、人物、沿革中回响。于是,便有了《漫话唐河》,这本记载着乡思乡愁乡变的书中故乡。
唐河,我的母亲河,你是唐河人灵魂深处的依恋。
(河南广播电视台 乔正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