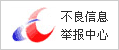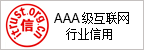上海卢湾中学的一名教师在家里为学生上“云班课”。 新华社记者 刘颖 摄 本报记者 罗娟
稍微犹豫了一会儿后,陈静把语文补习课程从儿子浩浩新学期的安排表中划掉了,取而代之的是少儿编程兴趣班。
这是浩浩自己的要求。
“8月29日,小学一年级、初一、初三、高一、高二、高三年级开学;9月1日,小学五、六年级,初二年级开学;9月7日,小学二、三、四年级开学……”8月9日晚上,陈静等来了这条堪称有“标志性”意义的通知——北京市秋季学期开学时间。
10天后,教育部发布《关于做好2020年秋季学期教育教学和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全面恢复教育教学秩序”几乎成为了所有相关新闻推送的标题。
看到各方表现出的积极坚定态度,陈静谨慎乐观地觉得,这一回,开学这件事,多了好几道保险栓。
1月17日,小学三年级学生浩浩迎来了2020年寒假。那时候,大概全北京城没有一个人会想到,像浩浩这样的四年级以下学生,整个春天和夏天都无法再返回校园。寒假,最终与暑假“无缝衔接”。
到秋季学期开启时,他们已经“在家上学”近8个月。

2月中旬,河北省邯郸市一名学生在家中通过网络直播接受线上教育。(新华社发)
不开学了
“到底能不能开学?”
陈静无法准确说出究竟是在哪一天,有人意识到当时正在国内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会影响到即将到来的春季学期,但她记得,随着手机上的日历从1月跳到2月,“开不开学、怎么开学、不开学怎么办”成为了各个班级群、妈妈群、辅导班群里被讨论最多的问题,“是每个家长的一日三问”。
在陈静加入的一个妈妈群里,有人感叹:当妈十几年,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却是第一次连孩子什么日子返校都搞不清。
答案来得不算晚。2月初,教育部提出“停课不停学”,要求开展“云教育”;2月17日,北京市中小学未能如期开学,在家上学模式正式开启。
定下神来,陈静摩拳擦掌踌躇满志。和所有选择“鸡娃”的家长一样,过去她总嫌周一到周五的学校教育进度慢内容少。按北京市教委要求,延期开学期间不上新课,尚处于弹性上班中的陈静觉得,利用网课,加上自己的安排督促,让浩浩疫情期间的居家生活成为一段高效的家庭教育时间不是件难事,“每天早8点到晚8点,从宇宙大爆炸讲到太阳系毁灭都够了”。
考虑到接下来一段时间儿子会高强度使用电脑,陈静还飞速购置了一台投影仪来保护他的视力。
无论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对9岁的男孩来说,假期延长都是一件值得高兴得蹦起来的事情,加上对着电脑上网课是件新鲜事,面对妈妈制定的包含语数外、体育、科学等科目在内的居家学习表,浩浩显得很配合。
第一天,浩浩认真上了3个小时数学辅导课,花了近两个小时阅读英文小说,还亲手种下一颗罐头含羞草——这是学校老师发来的居家学习指导包中的要求之一:种植物。
这样下去,从普娃变成学霸指日可待。陈静美滋滋地想。
第3天,每天浇水的罐头里没有任何变化,浩浩有些失望;
第4天,科学课老师在线答疑,告诉浩浩含羞草要放在向阳的地方,还可以每天写种植记录;
第6天,忘了浇水;
第7天,记得浇水,又忘了记录;
……
植物并不因为孩子的期盼或疏忽改变生长节奏,不知什么时候,罐头里冒出了4颗嫩芽,可浩浩的记录本,只写到第3页。
同样慢慢失去他注意的,还有各种网课。孩子天性好动,过去坐在教室里上课,难免也有走神的时候。现在面对一成不变的电脑屏幕,眼前没有来回走动的老师,身边没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同学,坐不住是必然的结果。
家庭教育计划实施一个多星期后,浩浩上每节网课的专注时间,已经超不过15分钟。陈静甚至觉得,只要网页一打开,儿子眼神就直了,身子也跟着歪了。
陈静自己也没能像之前设想的那样从容。快到3月时,她打算要研究的奥数书只翻动了几页。很多时候,她刚在书桌前坐下来,要不就是同事发来要修改或确认的工作,要不就是微信群里有人说这个网站可以抢购口罩那个平台可以下单买菜,再要不,就是厨房里的锅发出咕噜声,催促她起身去查看。
家里的客厅越来越像个小型机房。笔记本电脑、耳机、投影仪堆在一起,地板上铺满朝着各个方向的各色电线,陈静时不时要在浩浩的橡皮、卷笔刀下面找寻自己的工作文件。
收拾也没用,“早上起床拾掇了,不到中午又乱如麻”。
混乱中,一直摆在桌上一角的含羞草已经枝繁叶茂,可陈静和浩浩都没注意到,更没有伸手去感受它怎样害羞。
align="center">

延迟开学期间,小区里的空地成了孩子们为数不多的玩乐空间之一。 本报记者 杨登峰 摄
上网课好难
陈静的居家高效学习工程,推行不下去了。
目前在我国,仅是小学生的数量就超过1亿。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各地虽均推迟了返岗时间,但到2月底,全国大部分单位企业已复工复产。这意味着,整个春天,1亿多小学生的家长既要上班,还要操心孩子在家的生活和学习。
3月末,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发布了“疫情期间中小学生调研报告”小学篇。在陪伴孩子居家学习时,近三成参与调查的家长存在消极态度。28.2%的家长有打骂冲动,有7.3%的家长表示感到厌倦。
尽快开学,是陈静和亿万家长急需的救命稻草。
只是疫情不遂人愿。3月最后一天,北京市宣布将于4月13日起开展中小学线上学科教育。
何时开学,仍是未知数,但好歹熟悉的“课程表”又回来了。陈静重振精神想把浩浩的学习再次引入正轨,“哪知道,我自己就先被巨大的劳动量打败了”。
北京市级教育平台,西城区教育平台,企业微信,钉钉,腾讯会议,Classin……不同的课程答疑、作业提交都在不同的平台上。有的作业点点鼠标就交了,有的作业要拍照,有的作业要录视频,每天晚上,浩浩睡下后,陈静要花将近一个小时帮他交作业,这还不算之前检查作业的时间。
有一天因为工作太忙,陈静把交作业的事忘在脑后。接近夜里12点时,她的手机里收到了浩浩班主任王晓鸥的催促微信,“吓得我一下从床上弹了起来”。
王晓鸥同样盼望着早一些开学。她是浩浩的班主任,也是其他67位学生的班主任,但从2月中旬居家学习开始后,王晓鸥觉得自己更像是一个电商平台客服,还是24小时在线那种。
记录每个学生的体温,发布学校的通知、文件、资料,询问学生的思想、精神状态,这是她每天的固定工作内容。剩下的,就要看当天有多少突发状况。
每一个居家学习指导包发放后,不同的家长针对不同的内容会有不同的疑问;也有家长不会安装上网课的设备,王晓鸥要在电话里一步一步指导。
4月13日线上教学开始后,每天都有找不到课程资源包的学生和家长,也有不知道当天作业是什么的学生和家长,还有忘记提交作业的学生和家长。王晓鸥想不明白的是,一边有那么多人在出状况,一边又随时有作业提交到自己的系统端。于是,她还要时刻准备批改作业,反馈问题。
由于北京市采用了统一的课程资源包,王晓鸥和她的同事并不用备课上课。每一周,让她觉得自己确实在扮演“老师”角色的,只有6次线上答疑课和一次班会。与学生隔空一起看着教学视频,从业多年的王晓鸥根本不知道,有多少孩子在认真听课;在课堂练习环节,又有多少孩子真的动笔演算、抄写了。

手机和网络,是许多孩子疫情期间最“亲密”的伙伴。 本报记者 杨登峰 摄 疯狂的不是黄庄,是教育
4月的一个周末,陈静开车路过著名的海淀黄庄,发现那里静悄悄的。
北京教育看海淀,海淀教育看黄庄。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黄庄周边的道路永远都拥堵不堪。尤其在周末和寒暑假,路上全是背着书包上下补习班的孩子。
和旅游、餐饮等行业一样,海淀黄庄“疯狂”的补习产业的暂停键,是一瞬间被按下的。在标志性大楼银网中心里,大多数培训机构的大门从春节放假一直关到“五一”之后。
黄庄暂停了,疯狂的教育一点都没停。
眼见疫情在短期内不会消失,从2月份起,陆续有辅导机构通过与第三方平台合作将课程转移至线上,其中也包括了学而思、新东方这样的头部教育机构。
浩浩的奥数小班课就被平移到了线上。为表示诚意,培训机构减免了200元学费,还赠送了几节其他科目的课程。但这并不能让家长满意,“成本低了,价格为什么不下调?”“断线、卡顿,一节45分钟的网课要折腾近两个小时”……在辅导班的微信群里,家长们各有各的抱怨,说得最多的,是自家小孩傻乎乎地对着电脑屏幕上课,效果很差。也有家长就此要求退班退费。
“抱怨”并没有影响线上辅导课的热度。眼见浩浩对上网课越来越不耐烦,陈静便退掉了此前报好的英语辅导课,想换个稍后一些的时间。“可别的时间都报满了,一转身,刚退掉的名额就被人占去了。”打电话给辅导机构客服,对方态度很好,“但就是没办法再把孩子塞回去。”
陈静深感后悔。“哪怕孩子每节课就听15分钟,也比不上课强。”作为以前每逢假日就要到海淀黄庄报到的家长,她无法遏制这样的想法产生。
为了留住学生,匆忙转战线上的辅导机构使出了浑身解数。其中,过去限于场地始终“一座难求”的名师班不再限制报名人数,让许多家长大呼惊喜。
五年级学生维维和她的妈妈是陈静在海淀黄庄认识的一对母女。维维是个标准的“牛娃”。过去,受限于时间和名额,她只上了2个数学班,一个英语班和一个语文班。每堂课3个小时,加上老师拖堂和来回路程,大半天就没了。每次见面,维维妈妈都会诉苦,“太折腾了”。
疫情期间,维维平时不用上学,网课又可以回放,她妈妈一口气给她报了6个名师班——4个数学,两个英语,语文也增加了两个时间较短的打卡课。小姑娘学习能力强,又有超乎年纪的自律,一天能够完成20多项学习任务,“真希望以后都能上网课。”维维妈妈说。
只是并非每个孩子都是牛娃。名师在线上课一个月后,不少家长并没有在孩子身上看到预期中的进步。名师讲得太快,课程难度也高,很多一语带过的概念、方法普娃们根本不知道。还没回过神,一堂课已经结束了。
到底是名师成就了牛娃,还是牛娃成就了大师,这在课外辅导行业就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是门玄学。但经过疫情期间疯狂的线上教育,陈静渐渐意识到,过去包括自己在内的许多妈妈口中常挂着的一句话,似乎经不起推敲。
那句话是这样的,“如果我能帮孩子追名师,孩子一定学得更好。”
三好少年成了网瘾少年
5月13日,北京市教委发布通知,6月1日,高一、高二年级,初一、初二年级和小学六年级返校复课;6月8日,小学四、五年级返校复课,一至三年级做好返校准备。
就在陈静以为这个漫长的寒假终于熬到头时,6月11日,“西城大爷”确诊,北京连续56天无本地新增新冠肺炎病例的纪录被打破,随后,新发地疫情暴发。
6月17日,已返校的中小学生停止到校,而三年级学生浩浩,甚至还没来得及开学,就又“放假”了。
没迎来开学,陈静和丈夫张文松却迎来了状态日渐“不对”的儿子。
哒哒,哒哒,哒哒……坐在浩浩对面“监工”三四个月,陈静听到鼠标点击声的频率越来越高,甚至到了一刻都不停的程度。
可事实上,上网课极少需要学生使用鼠标,更多的是要拿起笔来练习。
留心观察后陈静发现,儿子成了个“鼠标手”。只要坐在电脑前,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他都会握住鼠标四处点击。哪怕陈静就坐在旁边,浩浩也忍不住在网页的各个角落东戳一下西戳一下,“根本停不下来,仿佛只有那种枯燥的声音能让他心安”。
有一天网课结束后,陈静调出了电脑里的浏览记录。一个半小时的课程里,浩浩竟然打开了40多个网页,网络小说,网页游戏,还有提供游戏直播的视频网站。总之,都与学习无关。
新冠肺炎疫情对青少年群体心理的影响远超一般人的预估。北京市青少年法律与心理咨询服务中心面向全国10万青少年开展的抽样调查显示,近半数受访青少年认为自己受到“憋闷”“恐惧”“紧张”情绪困扰,约三成受访者表示“全天基本离不开手机”,还有一成青少年“一天中什么也干不下去,就是玩游戏”。
浩浩也开始沉迷网络游戏。“和平精英”“第五人格”……陈静在平板电脑上频频发现一些类似的游戏图标。虽然她和丈夫一再告诫浩浩不许玩网络游戏并删掉了相关App,但孩子还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重新下载安装。
6月初的一天早上,陈静起床走进浩浩房间,见他歪坐在床上睡着,手里握着手机。陈静拿过手机按亮屏幕,游戏页面赫然呈现在她眼前。翻看游戏里的时间记录,浩浩应该是半夜3点多开始“行动”的。
脑子里嗡地一声,陈静顺手操起一旁不知是什么的东西,对着浩浩一通乱抽。被打醒的孩子先是一脸惊恐,随后开始哇哇大哭。
陈静崩溃了。她想不明白,半年前那个爱好是踢足球、打羽毛球和下围棋的少年,如今竟然熬到半夜,只为等父母睡着后安心玩游戏。
几天后,陈静和丈夫张文松带着浩浩一起坐在了儿童心理咨询师杨建利的面前。
这是杨建利接手的又一个疫情期间儿童沉迷网络案例。“你知道浩浩玩的是什么游戏,他又最喜欢游戏里哪部分内容吗?”面对一直在“控诉”孩子的张文松,杨建利的第一个问题就让这位爸爸答不上来。
杨建利告诉张文松,疫情期间青少年长期脱离集体生活,缺乏规律的生活,也缺乏与家人之外的同学、伙伴甚至陌生人的沟通,情感需求得不到满足,才转而用网络或游戏作为替代品。
这时,陈静想起,浩浩一位最好的朋友就住在同一小区,可两人在5月前都没有见过面。
第一次咨询结束回家后,按照杨建利的建议,张文松在平板电脑上安装了浩浩此前玩过的所有游戏,然后向他“请教”每款游戏的内容和特点。
“这个游戏讲的是三国英雄故事,赵云这个角色特别厉害。”听浩浩这么一说,张文松立即回应:“我觉得关羽更厉害,设计游戏的人大半是乱排英雄谱。”
为了验证爸爸的话,浩浩重读了《三国演义》原著的大部分章节。虽然得出的结论依然是赵云强过关羽,但也发现了游戏中诸多不符合原著的设定。
几天后,浩浩删掉了那款游戏。“他说再玩起来感觉很没劲。”张文松欣喜地向杨建利反馈说。
临时的玩伴,“临时”的童年
4月30日凌晨,北京市突发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一级响应调整为二级。5月1日,在王晓鸥和家长们的组织下,浩浩和全班同学去户外玩了一天。
这是1月中旬后,这群孩子第一次再见面。因为一天的相聚,浩浩开心了近一个星期,精神状态也随之振作了不少。
生于2010年后的北京,除了同班同学,浩浩这一代孩子只有“补习班玩伴”。
一起上补习班,意味着学习内容和时间都一致。可以一起做作业,也可以一起在下课后去便利店买零食,放学后再一起去坐地铁。上学期,浩浩的补习班在周六,好朋友的补习班在周日,两人一商量,要求两个妈妈想办法把时间调在一起。“必须!”浩浩他们很坚决,因为如果不这样,就不能一起玩,几个月下来,他们可能就不是最好的朋友了。
一家三口每周一次的心理咨询还在继续。到了7月,关于电子游戏的问题已经得到了各方都满意的解决。陈静和张文松不再把玩游戏看做十恶不赦的事,浩浩也不再偷偷玩游戏。按照和父母的约定,他每天有半小时时间,光明正大地玩游戏。
其余的学习外的时间,陈静鼓励浩浩到小区院子里玩耍。慢慢地,满头大汗回家后,浩浩会提起某个打水枪的玩伴,或者另一个捉迷藏的玩伴。
憋了一整个春天,孩子们很快玩到了一起。
进入8月下旬,陈静和张文松开始为新学期做准备。数学补习班、英语补习班依然要提前安排上,只是经历了与孩子一起在家上学的半年,陈静“鸡娃”的渴望变得没有那么强烈。她计划每周给浩浩留出一天的自由时间,由他自己决定要做什么;浩浩坚持要学的少儿编程也保留了下来,尽管按照大多数“鸡娃”父母的规划,进入四年级,所有的兴趣班都要让步于课外辅导,为即将到来的北京八中少儿班招生做准备。
“少上一节语文课程,让他保持自己的爱好,又怎样呢?”陈静看着眼前的新学期计划表,说服自己。
正是下午,窗外满是孩子们的呼喊声、打闹声。10岁上下的孩子,即使一起玩了好几次,也说不清每个人的名字。后来,他们干脆给每个人编号,“今天1号小朋友没来”“明天我要带变形金刚跟5号小朋友一起玩”。
陈静暗暗佩服孩子们解决问题的能力。只是仔细想想,她又觉得这像是一个隐喻。是不是连孩子们自己都知道,一旦新学期开始,这样的“临时团伙”就会解散,院子里又会恢复到往日静悄悄的模样?
责任编辑:梁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