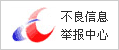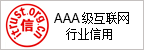《我的二本学生》 看见中国普通年轻人的命运
黄灯,湖南汨罗人,学者,非虚构作家,现居深圳。著有《大地上的亲人》、《我的二本学生》,曾获“琦君散文奖”、“第二届华语青年作家奖”非虚构主奖、深圳读书月2020年度十大好书、搜狐文化2020年度好书等,入选《环球人物》2020年度面孔。
《我的二本学生》 作者:黄灯
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0年8月
致敬词
2020年,青年一代的焦虑引发了广泛的关注。相比于985中自嘲为“小镇做题家”的高材生、在“绩点为王”规则中的清北精英,“二本学生”在各类社会范围内的讨论中常常沦为“沉默的大多数”。《我的二本学生》则将目光投向了他们,作者黄灯用她曾教过的二本学生们鲜活的经历,诉说这批年轻人在时代变迁下的困惑与失落,焦虑与希冀,思索时代环境与青年发展之间的关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的经历,折射出中国最为多数普通年轻人的生存境况。
我们致敬《我的二本学生》,致敬它用细致的记录,让一个个看似平凡却不平庸的心灵发出曾经不被听到的声音。我们致敬黄灯,从《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到《我的二本学生》,她用持之以恒的行动,实践着一名教师的人文关怀,和一名知识分子的社会思考与道义担当。
答谢词
从2006年到2019年,我在南方的一所大学当了两届班主任,完整见证了80后、90后两批年轻人的成长。在多年相处的过程中,直面他们学习、就业、考研、安居等各类具体的困境后,我总是忍不住拿自己和他们对比,并追问一些问题:为什么今天的年轻人,会毫不犹豫地认同个人奋斗的路径?为什么他们会将自身的困境更多归结到个人层面?为什么他们会自动剥离个体和时代之间关系?
我知道自己无法回答这些问题,更无法通过写作推出一个斩钉截铁的结论,作为社会转型的亲历者、见证者和介入者,我有限的记录,只是急速流转时代的一个剪影。从这个层面而言,《我的二本学生》,更像是一个人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对日常生活的观察和自省,它是开放的,未完成的,充满了局限和不完美,但它竭力打开一个话题,揭开帷幕,让更多的人看到自己以外的人群。我的写作,不过转身后,看到了学生群体,看到了世间更多的年轻人。
——黄灯
这本书
“相比理论的诱惑,我更想书写具体的人”
新京报:这本书的一个特点是对学生自述的大量呈现,理论分析部分相对较少。为什么选择这样的写作方式?
黄灯:关于本书的定位,我在序言第一句就讲得很清楚——这是一本教学札记。我在写作的时候,被无数的想法和无数年轻人的形象、命运变迁所包裹,我想表达一种建立在经验之上的复杂图景、和一种基于直觉的观察。
因为接触的学生个案极为丰富,学生差异极大,我没有办法穷尽我教过的所有学生,这就意味着,我必须放弃学术性的专著式写作。从方法论而言,我也无法统计所有孩子的具体状况,在证据欠缺的情况下,任何结论都是不负责任的。但我完整目睹、陪伴了80、90后两代年轻人的成长,我知道很多孩子成长的故事和秘密,和他们有深入的交流,这是我的优势。
任何一种写作都有局限性。相比理论的诱惑,打动我的是学生命运的流转。当然,理论的观照和对社会的透视,也是我写作过程中隐秘架起的X光机,但从这本书的定位出发,我还是竭力避免生硬的理论介入,只是在合适的时候,趁机表达自己的观点。
这是一本不完善的书,是一本局限性很强的书,但也是一本诚实、节制,严格遵循非虚构写作伦理和写作要求的书。正是因为它的诚实品格,才接通了很多人的共鸣情绪。
新京报:有评论认为,过多展开学生的个例,让本书探讨的一些有意义的问题浅尝辄止,使得全书显得比较零散,缺乏对问题的系统、深入的洞察。你怎么看待这些批评?
黄灯:站在读者的角度,可能会有这种想法。站在作者的角度,写作者只能依据他所看到和掌握的材料来书写,不能有半点越界。
我的写作是基于我在广东F学院的日常生活,主要就是上课(公共课偏多)、当班主任、导师制带学生这些繁琐的事情,这种结构的确定性,使得文本无法获得充分、系统、深入的讨论空间,加上脱离既定素材的讨论又会显得游离,我只得割舍。更重要的是,学生的成长因素特别复杂,很难和各种必然、偶然的要素建立因果关系。我既然选定了非虚构这种限制性极强的写作方式,记下他们的成长经历,是我最能把握、也最应该做的事情。
当然,我得承认,造成这种状况,和自己不成熟的写作有关。我还没能处理好材料的诱惑和问题指向之间的关系。
新京报:你在书中提到,与自己教的二本学生相比,“重点大学的孩子,仍旧以最古老的方式,端坐在图书馆阅读泛黄的纸质书籍”。联系高校“学术KPI”的现象,你怎么看待顶尖高校因为过度竞争的焦虑,“容不下安静读书的书桌”?
黄灯:我在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重点高校都待过,在这些学校里,我总能看到不少孩子还是以最传统的方式认真读书。那个时候,我就感慨,二本院校学生和他们的差异,可能是图书馆和高质量学术讲座的差异。当然,重点高校出现“绩点为王”的状况也是真实的,但有不少学生还是在安心读书。
在全球化出现挫折和分化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大家都在共同承受这一后果。从这个层面而言,我从来不认为我仅仅只是写了二本学生,他们背后实际上站着更为庞大的年轻群体。
这个人
“社会转型期的亲历者、见证者和介入者”
新京报:《我的二本学生》出版后,获得了非常多的关注。你怎么看待它的走红?你的生活有发生什么变化吗?
黄灯:这本书并不完美,它的影响力主要来自话题的重要性,来自社会对年轻人命运的关注、思考,以及对转型期社会走向的探索。我的写作,不过是提供了一个契机和切口,便于大家讨论问题。
除了要接受采访,我的生活没有太多改变。有意思的是,采访我的记者,95%是年轻人,是80后,90后。他们大部分都是名校毕业,不少有海外名校留学的经历。但他们普遍对二本学生的话题感兴趣。采访之余,我们会共同探讨年轻人的命运,会探讨社会、时代和年轻人的关系。
新京报:你在书中也提到“导师制”的实践。你不仅对文学课堂进行了精心的设计,还非常注重和学生的交流。这是一种有别于通行于目前国内高校体制化、标准化教学的“精耕细作”。现在还在坚持吗?“导师制”的意义是什么?
黄灯:我进行的“导师制”实践,是基于师生互信所建立的一种十分松散的“君子协定”。换言之,就是“学生愿意学,老师愿意教”,没有任何考核目标,也不进入学校的任何评价机制,当然,也没有经费支持,所以,它算不上“精耕细作”,纯粹是“业余施肥”。
我在广东F学院的时候,尝试“导师制”很多年。最近因为工作变动,调往了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暂时还没有施行。
“导师制”也说不上有太多意义,就是通过师生的协调和信任,去获得一种真正的大学生活的体验,获得一种因为思考和阅读带来的乐趣,让大家拥有一个交流和提升的机会。
新京报:2016年,你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曾引发广泛讨论。乡村书写一直是你关注的领域,你觉得那篇文章和《我的二本学生》之间,有怎样的关联吗?
黄灯:两者之间确实存在关联。我写农村儿媳这篇文章的动因,来自对年轻的侄子侄女命运的忧虑,他们作为留守一代长大了,但他们甚至连重复父辈的命运都不可能。后来写完《大地上的亲人》,我脑海中始终盘旋一个问题:那些比我年轻十岁、二十岁的晚辈,如果考上了大学,会如何?而我目前所从事的工作,恰好回答了这个问题。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刘亚光
责任编辑:梁辉